摘要:“毕摩”作为彝族传统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是彝族社会中“智慧”的化身,在彝族传统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曾与“兹、莫”同处于凉山彝族传统社会中的统治阶层,占据着彝族传统社会关系中的特殊位置。社会资本作为20世纪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赋予了“毕摩”独特的研究视角,社会学领域的“嵌入性”理论,更为研究“毕摩”这一社会阶层时诠释出其独特的运作规则、文化视野及社会效应,对于理解其在彝族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诠释。
关键词:毕摩;彝族;社会资本;嵌入性;社会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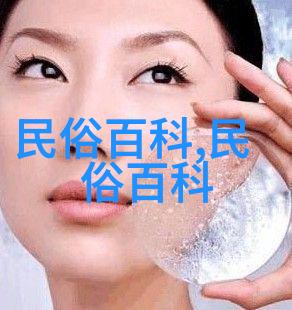
一、“毕摩”的本质内涵
毕摩,是彝族民间的社会知识分子,是念诵,以特定的仪式沟通、调解人、鬼、神三界关系的宗教职业者,是彝族多神崇拜信仰文化中集创造、传播、主持为一体的大成者。“毕”彝族语言为“诵、念”之意,“摩”即“长者、老师”,意为“念诵的长者或老师”,在《乌蒙彝族指路书·乌蒙卷》之《指路篇》中,以祖先崇拜为对象的西南彝族,作为送灵指路的毕摩,在彝族社会中深受爱戴与崇敬。在《乌蒙彝族指路书·芒布卷》中描述了毕摩不仅以牺牲用物和布插“神枝”为媒介,通过念诵和一定的仪式形式来实现人与神的沟通,更指导着彝族的社会“人事”。彝族典籍《百解经·献酒章》记载了毕摩历史地位及神圣职能。在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中曾出现过“兹(土司)、莫(法官)、毕(毕摩)、格(工匠)、卓(百姓)”的社会划分,毕摩作为社会阶层划分中的特殊阶层,据记载出现过三种职能:一是唐、宋以前,其名曰耆老及鬼主,担任彝族酋长,兼任祭司的职能,处于执政的地位;二是元、明至清初阶段,一般称为奚婆,为酋长的智囊人物和助手,处于佐政的地位;三是清初改土归流以后,一般称为毕摩,专司宗教祭礼一职及传播彝族文化。
1981年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社会学”,倡导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研究作为民族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李绍明先生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任何一个社会及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某一特定的民族共同体而单独存在,体现出民族的社会发展在具有可寻性共同特征的同时又呈现出不同特征,是一种以‘点’映‘面’的社会事实”。毕摩作为彝族传统社会中的特殊阶层,所实行的具有宗教色彩的信仰活动,不能被单纯的被解读为“迷信”,[2]无论是一度成为彝族社会结构中的执政阶层,还是当代极其特殊精神气质的文化,毕摩的研究对于理解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的彝族社会构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彝族传统社会关系的构建
在传统彝族社会结构中,“家支”仍旧是彝族社会的关系模式,是以父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团体。在整个彝族传统社会中,据记载有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和呷西五个等级之分,兹莫作为地位最高的统治者,曲诺是奴隶主阶级,曲诺相当于保护名,不具有奴隶的性质,却与奴隶主存在依附关系,阿加、呷西则是奴隶阶级。在一个社会阶层划分明确,社会角色及社会规范清晰的传统彝族社会结构中,一句彝族谚语“德古知识上百,兹莫知识上千,毕摩知识无数计;土司到来毕摩不起身,毕摩起身土司反常态”就可窥探出毕摩的特殊社会地位。
在《原始的宗教》中,列维·斯特劳斯引用原住民思想家透辟的观察说“一切神圣的事物必须有他们的地方”,这个观察主张地点的位置并不是任何地方,而是个别的每一个场合的严格而又正确的地点,只有在此处才能体现出他们的特点,具有“神圣”的效应。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现代社会世界高度分化后产生出来的一个小社会,毕摩作为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中相对独立的特殊社会关系,在特定的社会类型中形成了独立性“场域”,毕摩特有的祭祀仪式成为“符号”,成为交互“工具”存在于彝族社会关系结构网络中,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实在体,在自身这一主体范围及神职职能所能触及的社会关系网内,构建着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毕摩的特殊社会属性揭示着其拥有:与神鬼祖先,与神职仪式主人,毕摩与毕摩之间的三重社会关系。[3]
三、“毕摩”资本与彝族社会建构
(一)毕摩的社会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在198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首次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将其界定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并从实践领域出发认为 “每一种资本都有自己的符号形式亦为‘象征资本’”。[4]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1996)认为社会资本体现于社会里的凝聚力,表现为信任,他认为社会资本处于核心地位的信任,起源于宗教、传统伦理等现象,这种公共的信心既可以不断积累又可以投资于未来。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将社会或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哈皮特和戈沙尔将社会资本划分为:①结构维度,又称为结构性嵌入,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人格化一面,分析重点在于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的特点,即网络联系存在与否、联系的强度、网络的密度、中心与边缘、连接性等。②关系维度,称为关系性嵌入,通过创造关系或由关系获得的资产,包括信任和可信任、规范与惩罚、义务与期望以及可辨识的身份,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人格化的一面,即与社会联系的行动者有关,表现为具体的、进行中的人际关系,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建立的具体关系。③认知维度,是指提供不同主题间共同理解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如语言、符号和文化习惯的三重属性。而社会资本建构了社会结构,为个体行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资本的不断再生。[5]
毕摩作为彝族传统社会的精神信仰,在严格信奉“毕摩神”同时也遵循着一套完善的祭祀仪式,在作“毕”社会活动中,这种极具人性的信仰行为,使这些具有精神意义的宗教信仰在一个严格而又正确的活动地点实现了时空性的神圣转化,并在这个社会场域内实现了一系列的社会行为。毕摩作为彝族社会结构中的特殊阶层,以其特有的社会交互行为,成为彝族社会结构中实体性存在,通过毕摩信仰的神圣时间和空间,实现了作“毕”主体与祖灵信仰的互动,以毕摩为中心,彝族社会为边缘界限的时空社会中被建构起来,在这其中被彝族社会群体性认知且认同的信仰,是具有特定语言、符号及习惯的神圣仪式,作“毕”主体可按照需求进行祭祀仪式,呈现出一种理性化选择的模式,至此实现了毕摩社会行为的表现与实践的社会关系的整合。
(二)毕摩在彝族社会结构关系中的“嵌入”
“嵌入”概念源于卡尔·波兰尼的《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嵌入”原本指一个系统有机结合进另一个系统之中或者一事物内生于其他事物之中的客观现象。卡尔·波兰尼提出“经济的社会嵌入”强调经济活动是一个制度化的社会过程。格兰诺维特在1973年的《弱关系的力量》、1974年的《谋职》以及1976年的《网络抽样:初步准备工作》中强调:人必定存在非经济理性的行为动机。人的地位、权力和社会性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网络,所有的行动都只有被放大到社会背景下方能实现。强调经济的交易行为是被置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影响交易的方式和结果,是以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网络为核心的理论。毕摩作为一个独立化的社会阶层,在传统彝族社会结构中是具有清晰、明确社会界定的,其成员的资格和身份要经过神灵、社会、毕摩三方认可,不存在选择与被选择,是由历史、由具有毕摩“血统”且具有独有社会规则所共同决定。据记载,在凉山彝族传统社会中,毕摩沿袭仍旧持续着“家支传承”的社会结构,分为“毕摩、毕兹、毕惹”三等级,毕摩不论是学毕、行毕、游毕、分毕都承袭着一套严格的组织系统,毕摩世家按照代代相传、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在一个家族一个支系内部实行封闭式传承,由于彝族社会长期以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存在官方文书管理机构,其文献都靠毕摩自行整理保存。毕摩的传承形成了以家传世袭、旁系传承和自行作毕为辅的多层次结构,是由特定的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综合体现,在沿袭着以血缘为传承强关系的同时,毕摩游走于传统彝族社会的贵族、奴隶主、奴隶阶层时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纽带,其间所形成的弱关系成为自身获取社会资本的条件,也充当跨越社会结构与阶层界限去获取信息的桥梁,毕摩内的不同阶层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内流动,传递着信息,也创建和整合着整个彝族传统社会结构的流动。
1.结构性嵌入
毕摩作为彝族文化“智慧”的代表,文化精髓的传承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并没有形成多样化、统一化的传播模式,仅依靠其丰富的社会感知,运用宗教文字、独特的祭祀仪式和宗教教义编织完善传承体系。通过依靠规则、仪式程序和先例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络,是相对客观且可见的社会事实,以外在化的祭祀活动、行为交互到内在化的精神领域的承托与记载,都是毕摩与彝族社会群体共同意识下行为表现的社会整合。
2.认知性嵌入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无论是否将利益作为其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当其社会行为以物物或货币交互关系呈现出社会活动时,社会资本的流动便伴随着社会关系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进程,毕摩的宗教活动实现了毕摩祭祀社会行为职业化的转换,毕摩执行着沟通神、鬼、祖灵的职责,主祭祀群体获取的则是生活、未来的寻觅和对现实生活不安、顾虑的心理慰藉。至此毕摩与作‘毕’主体实质是依据各自不同的行为目的,实现了社会资本的交换,只是体现成为了表征性资本和实体性资本两种形式而已。
在毕摩作“毕”与主祭祀人选择祭祀方式的过程中,毕摩以自身的社会资本与主祭祀人之间构建了彝族社会关系网络,毕摩与彝族群体达成的互惠认同——“社会信任”,能够更为全面的诠释这一社会现象。马克·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网络机制的核心就是“信任”,即指出“经济领域内发生的交换行为的基础是双方建立一定的程度相互信任”,在作“毕”的资本互换的过程中,“信任”直接描述了毕摩与祭祀群体间的社会关系,主祭祀群体期待毕摩作“毕”带来的祛祸纳福,逢凶化吉的效应同时,毕摩获取的经济回报成为可认同性的关系性嵌入的表现,这种可认知性的关系性社会资本,是在共同的规范即社会价值观、态度和信仰中反映出的。
3.信仰的嵌入
涂尔干认为,宗教是一套与神圣事物相关的有关信仰和仪式活动,宗教被誉为“精神经济”,本身包含着“仪式、情感、信念和理性化”四个外在因素,而毕摩作为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神职人员,建构了人人之外的人神社会关系。这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会资本,在基于血缘之上的强关系促进了整个彝族社会的认同,某种程度上成为整个社会宗教信仰的取向或推力,体现的是信仰下强弱社会关系的整合,也是整个社会结构人际和情感的依附现象。
毕摩良好的职业形象和声誉,离不开其严格恪守的传承制度,更因为其代表着一种社会“平等”的理念,即使在传统彝族社会结构中有高低社会等级、贫富之别,毕摩作为德高望重的阶层在祭祀时必须平等待人。至此作为嵌入于彝族社会传统结构中的特殊化社会事实——毕摩,因信仰扩大了其社会资本的来源,也规范着宗教行为的发生与发展。
四、嵌入性理论视野下的毕摩社会关系
在彝族传统社会中毕摩的社会行为实质体现着一种“动态”关系互动模式,毕摩离开了其特定的地缘环境和神圣时间,也无法传承出特殊化的社会行为。布迪厄的《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强调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受到阶级、地位的决定性影响,不同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品味。布迪厄强调的“信仰区隔”,不同的信仰其实也能够形成不同的社会地位,即使一个人具有自己所选择的信仰和信仰方式,但是信仰也只能够通过其手中的权力表达与实践。实际上毕摩所依附的生存环境就是其不断嵌入、不断博弈的过程与结果,毕摩通过一种认同与皈依,通过其拥有的文化资本,不断在社会结构中进行建构和定位。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指出:“一种社会定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络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这一身份成为某种类别并伴随着规范约束,也蕴含着特定的职权与责任,被赋予该身份的行动者充分利用或执行这些东西,构成了与此社会位置相关联的角色规定。”毕摩这一极具宗教色彩的社会行为,在跨越现实与世俗后,以神圣的姿态成为彝族群体中实质的“关系存在”,它应该是理性化的进程,同时嵌入于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之中,而毕摩个体社会关系的丰厚,所能获取的神伦关系、神圣资源也会变化,毕摩的生活方式、阶级地位和经济模式等社会资本都在不断嵌入中伴随着毕摩社会属性的确立而深化,人人与人神的互动与契合,更强调出毕摩社会行为的特殊化互动模式,如果将彝族社会结构作为背景,毕摩在其“关系”内便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与界定,也促成了其“关系与资本”的实现与发展。
至此,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去考察极具宗教色彩的毕摩社会行为,不仅反映的是彝族传统社会的结构、文化、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更应该探寻一种根源于彝族社会结构中的精神文化的影响,这对理解现代化的彝族社会结构是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的。
这里是彝族文化网络博物馆,海量的数据,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是向世界展示彝族文化的窗口,感谢您访问彝族 人 网站。参考文献:
[1] 李绍明.论我国民族社会学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1982(4):72-76.
[2] 巴莫尔哈.四川彝学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77.
[3] 何耀华.彝族社会中的毕摩[J].云南社会科学,1988(2):17-21.
[4]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74.
[5] (美)泰瑞·雷.宗教资本:从布迪厄到斯达克[J].李文彬,译.世界宗教文化,2010(2):16-20.
作者简介:王瑶(1986—),女,彝族,四川西昌人。重庆,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
原载:《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3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